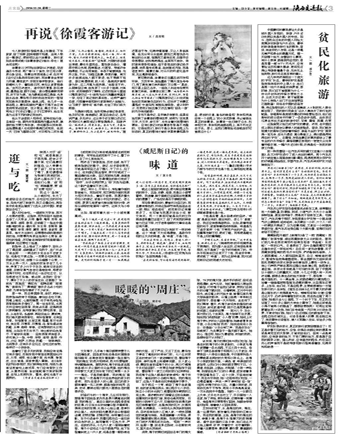文友周子,几乎每个周日都要带妻子儿女回趟老家。回老家后他总是在村里随走随拍随写,在微信朋友圈里晒一些主题为“我的周庄”的图片和诗词,图片朴素唯美,诗词酣畅淋漓。据我所知,周子的老家在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北山旮旯里,他的周庄并非散文大家王剑冰笔下的江南第一水乡――周庄。于是我就猜想,“我的周庄”里的“周庄”一定是周子对生他养他的故乡的爱称。因为在很多人的心里,自己的故乡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美,都是绝版的纯秀、古典、安详,最接近现代都市人理想生活的理想状态。
时逢初冬的一个周末,几位好友相约,跟随周子回他老家丹凤县蔡川镇庵底村探望“我的周庄”。通往山里的水泥路像竖笔的狂草,行云流水似的绕着山根尽情挥洒,偶有往来的车辆,礼貌小心地让道,像淳朴的山里人。浅笑的阳光最喜欢在山野里捉迷藏,时明时暗、时隐时现,涂抹着远山近影。车子行进途中,我看见路右边一座石桥的白色护栏上,刷写着两个红色大字:严庄。在桥的尽头,十几户人家一溜烟挨着坡根。周子介绍说这个庄子都是严姓,他下车指着斜坡上一户人家,说是去看一眼卧病在床的大姐。过了严庄,又过了王庄,最后车子停在了庵底村村委会门前。七八位村民正在村委会门外一家店铺前忙活,看到周子回来,亲热地凑上来嘘寒问暖。女人家心细,靠到车窗前逗周子的小女,再三叮嘱周子夫妇返回时,一定要去她家带些柿子回城。看到周子一家三口和村民们这样熟稔,我问周子这些人都是你家亲戚吗?周子笑笑说:“庵底村的小名就叫周庄。我的周庄到了,这些人不是叔伯兄弟就是婶子嫂子。”
车子拐过一个弯,就到了周子老家屋前,他的家在周庄西头,离公路仅七八步远,跨过小小的木头院门,就看到面东朝西的三间土房。虽然朝东的门面墙经过粉白刷新,但檐间的木椽和门窗,面容沧桑而斑驳。石砌的小院窄不过六尺,石缝间的车前草无摭无拦伸展着耳叶,灶屋房顶的瓦片,灰褐而深黑,长满青苔。一米阳光从房顶斜射到院内,忽然间有如步入江南人家,一种恍若隔世的寂寞与神秘。角落里躺着一片菜地,菠菜们睡眼惺忪探头探脑。后院关闭的两扇木门被岁月漂洗成灰白色, “咯吱”一声打开,抬眼一看,树在身边挺拔,山在眼前突兀,蓝天在头顶徜徉。
须臾,周子的媳妇找回出去串门的周大娘。78岁的周大娘,虽然手执拐杖,但说话思路清晰,底气充足。她忙着催促儿媳给我们做饭,叮咛周子给我们添茶,带我们去院外的山墙下晒太阳。山墙朝南,正对中午的阳光,透过墙上的方格木窗,能看见室内周大娘临窗的卧床。山墙上挂满一串串削过皮的柿子,像挂着一大片柿帘。坐在帘下,我们喝茶、看天,听周子叙说房前屋后的奇石古树,叙说家道中落、院子已是荒草遍布的邻居二伯家的往事……面对儿子、孙女,面对我们几个生面孔,周大娘禁不住欢喜,她向我们讲起她家“小人精”的事,她说上次周子带5岁的女儿回来看她,她患感冒身体不适,小孙女唤她“奶奶”,她恍惚间问小孙女:“你是谁?”小孙女喊了声:“我是你孙女”后就哭了,为此事孩子一整天都不高兴。她伤心、难过呀,她以为最爱她、疼她的奶奶,老糊涂到不认识她了。
谈笑间,周子的媳妇来叫我们吃饭,饭是在村前周子的小妹家做的。小妹家与周子家隔着一条水泥路,不过三四十米远。母亲不习惯去县城周子和商州二儿子家住,非要独自一人待在山里老屋,平日里照料老人的事就落在同村的大哥和小妹头上。在周子小妹家的院子里,一桌色、香、味俱佳的农家饭菜,让我们对小妹的厨艺赞叹不已。“小黄猫,别乱跳,上锅台,打断腿。”小妹一声吆喝,刚溜到灶房门口的小黄猫,赶紧缩着身子跑到墙角去了。这个小妹,不但麻利能干,而且伶牙俐齿,她一边招呼我们吃饭,一边嘻逗着高一声低一声不停喊她“姑-娘”(姑妈)的周子的女儿玩。打量小妹的家,四间砖瓦房干干净净,两间小平房亮亮堂堂,一方水泥院平平整整。她的一儿一女都已上大学,丈夫也外出打工了,平日里她一人在家,除了种地,照料母亲,还操持着一间磨坊。每逢周末只要哥哥们回来,她都会早早备好饭菜,等着亲人们回来团聚。
王剑冰的笔下,水,是周庄的床。周庄,是一位清秀的,散发着无尽韵致的江南女子。而在我的眼里,土地,是周子的周庄的根,亲情乡情,是周子永难磨灭的故园情结。留守在村里的父老乡亲,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播种、收获,守着安宁、也守着期盼,守着人世最简单、最深厚、最朴素、最温暖的情感。(作者供职于丹凤公路段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