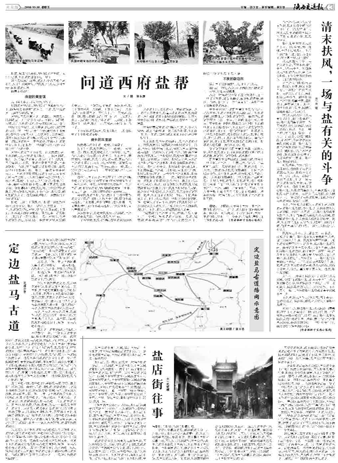盐帮,与现代人来说,早已成了陌生词。而细细追溯,他们的消逝也不过一甲子。
时间是戊戌年深秋,我们几个志同道合者相约,从千阳县城出发,经凤翔,到扶风,搜寻西府地区盐帮的印迹。
但愿不虚此行。
消逝的黄里镇
风自关山来,把千湖彻底吹冷了。
眼前的黄里古镇,早已没了“渔船来往暮烟中,鹅鸭河边水映空”的诗意。有的,是轻舞的黄叶,落在静谧的湖面。
黄里过去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。尤其是明清时期,街上开有许多车马店、粮油店、铁匠铺、药铺,大户人家的石狮、拴马桩随处可见。也有一些历代高官显贵、文人墨客路过此地时题写的石碑。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修建冯家山水库时,这些碑石连同村庄,或被迁移,或被淹没。现在村民们居住的台塬,已是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三次搬迁的家园。尽管如此,在新村庄的某些杂草丛中,还能找到一些残损石碑、石条石板等有些年代的物品。
黄里村的文书王双乐是一位文史爱好者。他小时候见过村里的能人张万一。民国时期,张万一从青海,经平凉,把盐运到千阳或凤翔。去青海时,把千凤一带的物品带去交易,回来时驮盐。当时,在青海露天采盐场装盐,都是按牲口个数来计价。张万一每次牵十来匹马,把三四匹拴在盐场就近的车马店,只牵五六匹马去装盐,叫人家给每匹马多装些盐,付钱之后,再返到车马店,进行分装,这样算计下来,每匹马驮盐都不吃力,最主要的是还省了钱。驮盐最担心的就是过河,有些没经验的脚夫,在马驮盐过河时,不小心会把盐浸湿,那可就损失大了。这是解放后张万一时常说给王双乐的闲话。
盐道上,时有土匪骚扰。盐帮有时就散些钱物,买个平安。张万一活泛,好交朋友。有一回,他的驮队经过黄里,被当地土匪截道,土匪们把他五花大绑准备勒索。匪头过来一看是张万一,就给手下交代,张万一是咱黄里人,今后他的驮队路过,不得打劫。但走出黄里,可没那么幸运。有一回驮队过平凉的一座独木桥,就有土匪在桥另一头等候。土匪故意牵着一头小毛驴挡住盐帮去路。同行人中,有一习武者,箭步上前,用力将那毛驴扛在自己肩上,又走几步,把毛驴放到河边,“等路的”一见此情,不敢再滋事。此后,张万一把习武者拉来给自己当下手。
王双乐说的是民国,是能人张万一,却也说出了半个盐道的辛酸。
漫长的五里坡
历史遗忘沟壑中的一道坡,太容易了。
从千阳到凤翔交界处,有一道坡,叫五里坡。顾名思义,就是坡道大约有五里长。过去,当地人做着给马帮拉车的生意。他们养牛,常在坡底下等候,凡是有路过的马帮,要借当地百姓的牛帮着把马车拉过五里坡。如果是马直接拖货,就由牛马共同分载,待拉上坡,再把货物装到马或者马车上。至于延续几百年,无从知晓。
这些年,西千公路(西安至千阳)在彭祖塬改道,宝平高速(宝鸡至平凉)在五里坡架起了一座特大桥。于是,五里坡彻底被废弃。今天去看,雨水冲刷沟渠,早已使那道坡面目全非。而荒草和落叶下,前人铺垫的砂石依然可见。
关于凤翔的官盐,当地史料中有这些零散的文字:“凤邑自前明万历四十年前,原食小花马池盐,并未输课,后改食晋盐,遂纳盐课。既而晋盐难行,仍食小花马池盐,并惠安堡盐,而纳晋课如故。”
短短数十字,却道出凤翔府明清时期,百姓食盐的来龙去脉。当然,这是官方记载。
上了五里坡,就是彭祖塬,这里的时光依然很旧。
贫瘠的土地、边缘的村庄、空寂的院落。火红的柿子挂满枝头,却毫无采摘的痕迹,就连狗的叫声和花猫的步子都显得如此懒惰。好在村里十多颗粗壮的槐树,告诉我们这里曾有过的厚重。
在与喧嚣隔空的彭祖塬村行走,几个老人显然把我们当做稀客。随意说起盐帮,他们你一句、他一句的,竟然给我们啧啧不休地拼凑出一段往事。
他们说盐是官府的钱袋子,是百姓的命根子。在凤翔流传着晁黑狗火烧盐局的故事。清末,官府对食盐销售有规定,武功以西只能销售花马池盐。清政府为了搜刮百姓,食盐由官督商办,在凤翔设有官盐总局,凤翔府所属的各县和虢镇、蔡家坡设有分局。盐局设立后,只允许买官盐,严禁百姓贩私盐,盐价也由原来的十六七文,上涨到六七十文。盐局卖盐也特别克扣,他们用碗量,百姓花一斤盐钱,只能买到九两。盐局设盐勇,在路上设卡检查百姓购私盐,盐勇经常勒索驮盐的脚夫。一次,麟游县分卡的盐勇一次就扣了盐帮60多头牲口。脚夫们忍无可忍,决定讨说法。依靠驮盐为生的凤翔人晁黑狗带领诸多脚夫,冲到凤翔官盐局评理无果,放火烧了官盐总局,大火蔓延,差点还烧了骆驼场。随后,他们还杀了盐局一差役。事情后来闹大了,岐山、扶风、眉县一些盐务分局也被砸,陕甘总督为了平息事态,撤销了凤翔盐局和诸多分局负责人的职务,并派兵七八百人前来凤翔镇压。不久,将为首的晁黑狗等人杀害。
“晁黑狗给百姓出了气,应该算是英雄吧。”一个戴着鸭舌帽的老汉说。是的,晁黑狗后来确实被记在当地文史资料中。但没有评论他是不是英雄。
不衰的新店街
沿着西千线继续东行,过岐山,到扶风。
新店街正在过古会,公路两侧摆地摊的足有一公里,车速只得减慢。
古会上销售的货物除了现代制造外,还有一些手工制品,如梨木案板,藤条编的笼、簸箕。当然,也有开着三轮“蹦蹦车”叫卖盐醋辣子等调味品的商贩。
出生于1936年的罗西章先生是当代著名考古专家,他的老家就在扶风新店街。他小的时候,时常能见到驮盐的骆驼队。每次经过的骆驼至少有二三十只,有时候能达到五六十只。至于盐来自哪里、用啥装、运到哪?他们那些孩子不大操这个心,他们感兴趣的是骆驼队炸的油饼,孩子们叫它“骆驼油饼”。盐帮的人有些是少数民族,吃不惯汉人的饭,就带着锅灶,走到大的镇子,就地架起锅灶做饭。每当炸油饼时,孩子们就围在跟前边看边流口水。盐帮的人总是撕一片给他们分着吃。
除了骆驼油饼给罗西章先生留下深刻印象,另外就是孩子们打闹时说的顺口溜:“谁打我的脚,变骆驼。骆驼驮盐,我吆脚!”
罗西章先生还告诉我们,解放初期,在关中一些山区,老百姓有一种常见病,当地人叫“瘿呱呱”,实际上是甲状腺肿瘤。要消灭这一地方病,有效的办法就是食用碘盐。山区百姓居住分散,文化知识落后,政府就派人去做动员,叫大家都食用碘盐,有些人就说:“瘿呱呱是咱山里人生就的骨头、长就的肉,这和吃盐没有关系。”还有些人说“姑娘吃了面面盐不生娃”。百姓把碘盐叫“面面盐”。因此,有些人宁肯翻山越岭去背青盐,也不吃碘盐。后来政府禁止销售青盐,才渐渐改变了百姓的食盐习惯。
后记:一路探访,对于关中西府一带百姓日常食盐的产地,上了年纪的人都不能准确说出来。但大体上可以确定,自明清到民国,西府一带的食盐,基本上有三个来路:青海盐,晋盐,还有陕北的花马盐。 (作者供职于宝鸡公路局)